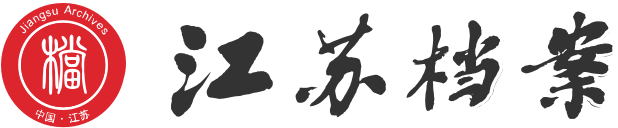- 信息时间:2021-04-20 15:20
- 浏览次数: 162
【导语】1996年9月,国际档案理事会(ICA)于北京召开了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并在此次大会上讨论、通过了《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ICA Code of Ethics)(以下简称《准则》)。此后,《准则》被陆续译为24种语言,以供各国档案工作者参照执行。其多维度、系统性地规定了档案工作者所应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即使在20余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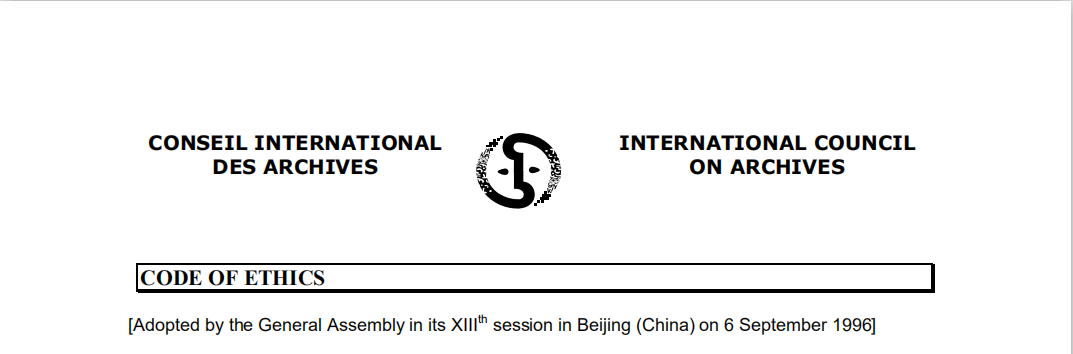
No.1 内容回顾
《准则》的内容包括“导言”和“道德准则”两个方面。“导言”共六条,主要讨论了该准则制定的目的、宗旨及应如何执行,而正文“道德准则”共十条,较为详细系统地为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划定了道德规范。接下来就让小编带大家回顾一下吧!
(一)说明
1. 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应为档案专业活动建立高的专业标准,使档案专业的新成员了解这些标准,有经验的档案工作者知道他们的专业职责,并促进公众对档案专业的兴趣和信心;
2. 本准则所使用的“档案工作者”这一术语,是指所有与档案保管、保护和管理有关的工作人员;
3. 应鼓励所有档案保管与服务机构制订和采用有利于实施该准则的方针和实办法;
4. 制定本准则的宗旨,是为档案专业工作人员提供一个指导性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为解决某些问题所提供的专门办法;
5. 每条准则都附有阐释,准则与阐释加在一起组成该道德准则;
6. 是否执行该准则,由各档案机构或档案专业协会自行决定;如认为合适的话,可对非道德行为进行调查,实行制裁。
(二)道德规范
1.档案工作者保护档案及相关资料的完整与安全,以确保其作为历史证据的可靠性。
档案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他们所保存的文件的完整性。在实施这个任务时,他们必须考虑到保管机构、文件产生单位、文件主题和利用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合法(有时是相矛盾的)权利和利益。客观公正是对档案工作者专业能力的一个衡量标准,他们应该坚决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为隐瞒和歪曲事实而要求篡改文件或档案等历史证据的压力,努力维护历史的真实。
2.档案工作者应从历史、法律、行政、治理等角度,对档案文件、资料进行筛选、鉴定和保管,切实合理地运用来源原则,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
档案工作者应当根据普遍性的、科学性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工作,必须根据档案管理原则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原则包括对处于不同运动阶段中的文件或档案的有效控制、保护和处置原则,对具有国家和社会价值的档案的鉴定与移交原则,对档案进行安全保管和保护的原则,以及档案的整理、著录、出版和信息提供利用原则等。
档案工作者应当熟悉文件产生机构的历史沿革和文件收集政策,并且依此对所接收的文件进行公正的鉴定,并能尽快地根据档案原则(如来源原则等)及公认的标准,对选择移交进馆的档案进行整理和著录。档案工作者应当根据他所在档案机构的经费和任务接收档案,接收时不应损害档案有机体的完整与安全,他们也应当进行必要的合作,以确保接收的档案保存在最合适的库房内。档案工作者应当努力维护国家历史文化的完整,积极参与对散失境外档案、文件的征集工作,参与国际间的合作。
3.档案工作者在进行档案的整理、保护和利用工作中,应当保护档案的证据作用。
档案工作者在进行档案文件的鉴定、整理、著录、保管、提供利用等项档案管理工作中,应当确保文件(包括电子文件和多媒体文件等非传统型文件)的档案价值。利用者利用的案卷中如有不对社会公开提供利用的档案需分隔抽出,须向利用者说明。
4.档案工作者应当确保档案所含信息的连续性。
档案工作者面对档案处置事宜时,首先要考虑保存那些反映文件形成者主要活动证据的文件,但也要考虑档案用户的利用需求及其变化情况。档案工作者必须懂得,收集来源不明的文件,不管其如何重要,都可能会导致不合法的商业活动。他们应当同司法部门合作,对盗窃、贩卖档案的人进行必要的处罚,并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5.档案工作者应当对他们从事的工作活动进行记录存档,并能对其工作进行辩护。
档案工作者应对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作好记录,并在采用新方式和新信息管理方法时与文件工作者进行合作。他们不仅要收集现有的文件,还应保证从一开始就将现行的信息和档案体系结合纳入与保存珍贵文件的工作程序中去。档案工作者应保存关于文件或档案的接收、保护和全部档案工作活动的永久性备案记录。
6.档案工作者应当尽可能地提供开放档案信息,为档案利用者提供公正的服务。
档案工作者应对所保存的档案进行编目,以便为档案用户提供公正的服务。档案工作者应以合作的精神答复用户提问,尽可能地鼓励档案用户根据档案机构规定、档案收藏情况、法律法规标准、档案所有者权益、寄存及捐赠协议等,利用他们所保存的档案。他们应当忠实地遵守和公正地履行文件收集时达成的所有协议。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社会文化作用,应当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档案的利用政策与规定。
7.档案工作者应该遵循利用和隐私双向原则,遵守有关的法令法规。
档案工作者应注意保护集体和个人的隐私及国家的安全利益,不得随意销毁档案,尤其是易于更新和损失的电子文件信息。除遵守档案法以外,还需要遵从刑法、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保密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知识产权法等各种法律。档案工作者应当保守所管理档案信息内容的机密,增强保密观念,培养良好的保密习惯,并且在档案管理实践中同各种失密、泄密、窃密行为作斗争。
8.档案工作者应当珍视国家和社会给予的特殊信任,并在实际工作中,不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求私利。
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其专业“特权”,约束自身的行为。档案工作者不应在工作中“捞取好处”,或者从事不利于档案机构、档案用户及专业同行的个人活动。档案工作者可以利用自己所保存的档案信息,进行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文化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与出版活动。
但是,这种工作必须在与其他档案用户同等的利用条件下进行,即不应该利用工作之便泄露不宜对社会公开的档案信息内容,不允许私人性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干扰所在单位的档案专业活动的正常进行。档案工作者若想使用版权所有者未发表的档案史料,必须首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9.档案工作者应系统地持续地更新档案专业知识,卓有成效地做好本职工作,共享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等方面的基本素质,不仅是从事档案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档案工作者应当加强自身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就现代信息社会的客观要求而言,档案工作者一般应当努力使自己具备四个方面的知识储备,即法律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哲学理论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
同时,有关档案工作者还应努力学习现代信息技术,以便使档案事业适应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此外还应努力运用专业知识,献身所从事的专业机构和人类社会的文化建设事业。
10.档案工作者应当通过与其他专业工作人员的合作,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提供利用。
正如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期间,国际档案理事会和国际图书馆联合会联合签署的《北京宣言》所言:“我们两个专业在道德价值观方面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无论从道义抑或法律意义上讲,都肩负着共同的责任,那就是保护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识和社会存在绵延繁衍而不被割裂,并为其产物的免费利用提供服务。
无论图书工作者还是档案工作者,为其相应的利用者提供服务,都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档案工作者应努力加强与专业同行的合作,避免发生冲突,以遵守档案标准和职业道德来解决困难,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专业人员的合作。
No.2 时代新解与讨论
伦理道德维系着文明社会的建构与发展,并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档案职业领域也概莫能外。但道德又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档案领域所面临的职业道德要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此,学界在1996年所提《准则》的基础上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多学科多维度地对当代档案职业所面临的道德挑战与要求提出了符合现世的时代新解,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正义之争:程序正义vs实质正义
著名档案学家琼·施瓦茨(Joan M.Schwartz)和特里·库克(Terry Cook)指出:“通过档案,过去被加以控制,某些叙事被特权化而另外的叙事则被边缘化......在档案利用和沟通的模式中,档案工作者持续地重构、重新阐释及再造档案。”由于现代民权运动兴起、后现代主义盛行等原因,档案与叙事、与权力的关系日益被人们所关注,档案记叙故事,而故事又关乎一个族群的认同与存续,故而档案也必然关乎社会正义。也正因如此,新时代里档案工作者传统的“中立立场”日益受到挑战与怀疑,学者们对档案职业与社会正义到底应保持何种关系而争论不休,并形成了“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
“实质正义”派以维恩·哈里斯(Verne Harris)、兰达尔·吉莫森(Randall C.Jimerson)、温迪·达夫(Wendy M,Duff)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档案职业长期作为权力同谋而存在,故而《准则》中提及的“中立立场”本就不存在。此派别主张档案工作者应该利用其职业特殊的记录性质与权力属性,积极投身社会正义事业,利用档案为少数族裔发声,为社会正义张目。档案工作助力解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为美国非裔梅毒实验索赔等都是该派所推崇的经典案例。
而“程序正义”一派以马克·格林(Mark A.Greene)、理查德·马修斯(Richard J.Matthews)、苏珊·奥波特(Susan Opotow)等人为代表,此派别认为正义是具有时代和文化特征,“实质正义”所追求的普世价值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且若档案工作者为了其所理解的“实质正义”而去刻意挑选所应归档的类别,则会损坏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并最终有损未来相关研究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这显然违背了《准则》的第1条。此派别强调,程序正义下的档案职业伦理主要就是工作者持久稳定地遵守特定时空中的职业规范,而非因“各自认为正义的立场”使档案成为各种政治主张的附庸。针对利用者提出的不公正的利用需求,档案工作者则应遵循《准则》第6条,向“所有利用者”提供“公正的建议”。
归根究底,“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非水火不容,双方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档案伦理与社会正义间的和谐共生,只是在观念认识层面有所不同。可以预见,两派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现有《准则》也将在这论战中不断修改完善。
“档案焦虑”:数字时代的新兴难题
“档案焦虑”一词由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J. Cox)首次提出,其认为由于特殊工作性质,档案工作者常可接触到组织中的大量信息,也因此会了解组织的种种“龌龊之处”,故而当面临公私选择时,档案工作者就很容易陷入伦理困境。而随着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档案不仅数量暴增,内容与来源复杂程度也日益上涨,这些都加重了档案工作者的无形压力,也形成了新时代的“档案焦虑”。
新时代档案焦虑多集中于“数字时代叙事权的再争夺”“遗忘权与隐私权平衡难题”“多样化利用需求”这三个方面。数字时代赋予了每个人发声的权力,却也带来了多元主体相互纷争、身份政治束缚个人等问题,而数字技术对隐私权的侵犯亦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些新时代的“档案焦虑”在1996版《准则》中要求对档案进行保管与鉴定的第1-2条,要求对所有利用者提供服务的第6条,以及要求尊重隐私原则的第7条都有所体现,但诞生于计算机网络快速发展初期的《准则》,显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的今天。若想消解“档案焦虑”,档案工作者就需要对自己的职业进行重新定位,成为一个“记忆建构者”而非单纯的“档案保存者”。而相应的,他们也应对本行业的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在原有《准则》的基础上完善并建构出新的职业道德规范。
文化差异:中外差异下的职业伦理区别
不同的文化会孕育出截然不同的道德伦理,档案职业亦是如此。跨文化研究领域中有一项极具代表性的成果名为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它使用“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 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以及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term versus Short-term)”这五个维度来解释民族文化对员工价值观的影响。若从这一理论对中外档案界职业差异进行探究,则可发现多维文化带来的不同伦理差别。
例如,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研究中,中国的弱势群体对权力分配不均的接受程度普遍比西方更高,社会更是长期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即权利距离较高。而这在档案领域就会影响到开放的普遍性与服务的均等化,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普通公众对档案的利用。而对集体主义的推崇也使我国的档案工作者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社会的记忆保存者,更强调以建立法规、明确体制等方式来建设职业道德,这与热衷追求个性化服务的西方档案工作者无疑是迥然不同。
此外,对长期导向的注重也使我国的档案职业更注重于顶层设计与长期发展,与相对更注重短期导向与具体问题的西方国度有所区别。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我国与西方国度的档案职业定位可谓差异明显,因此在档案职业道德的具体落实方面也必然有所不同,生搬硬套《准则》则不能适应当前中国档案管理的具体情况。
No.3 结语
《正义论》的作者,伦理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曾指出,“人类社会的伦理向度失落了,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可见伦理道德对日常生活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ICA于1996年制定的《准则》,正是当时档案界为建立全球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共同提高工作者素质水平及档案服务质量所做的努力结果。尽管25载光阴逝去,《准则》的基础规定对当代档案职业发展依然有其独特参考价值,而档案界持续不断的新兴讨论也会对其不适应当代之处进行修改完善。小编相信,在各位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之下,《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必将不断进步,适应档案职业的当代现状,并促进其未来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 :
[1]徐玉清.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J].中国档案,1996(11):40-41.
[2]李思艺.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中外档案职业伦理差异研究[J].档案管理,2018(05):22-25.
[3]王天泉.携手奔向二十一世纪──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图联联席会议草拟《北京宣言》[J].中国档案,1996(10):11.
[4]陆阳.档案伦理与社会正义关系研究的深层解读——基于实质正义观与程序正义观的冲突[J].档案学通讯,2020(06):22-30.
[5]张晶,陆阳.档案焦虑与新使命:数字时代档案职业定位再思考[J].山东档案,2018(06):7-10.
编译&撰文:孙辰睿
排版&美工:马海杰
选题&校对:龙家庆
来源:2021.04.06 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