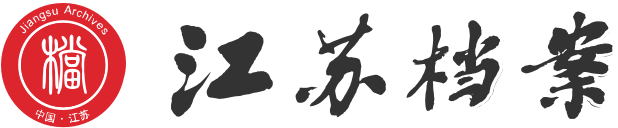- 信息时间:2021-02-03 10:27
- 浏览次数: 89
南通市档案馆 朱江 朱慧
档案编研是档案部门通过对馆藏档案的研读、挑选和整理,主动向社会提供档案信息的工作。编研作品的优劣是体现档案部门文化品位的一个标准,而学术性则是编研作品的核心价值,也是编研作品能够服务社会、有长久存世价值的基石。本文以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编辑《海韵江风两地缘——张謇与近代上海》(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下文简称《张謇与近代上海》)为例,从编研作品的题材确定、内容加工、质量保障等三个方面,探讨档案编研作品如何保证学术性。
1题材的确定与系统的研读
对于学术的理解,众说纷纭。笔者认同张威、谢镒逊的观点,认为“学术是指在拥有大量知识基础上对未知的研究行为,研究行为主体一般是某研究机构或其中的个人,或占有了大量研究资料的个人;研究内容是某一学科领域里的问题;研究性质是理论性的而非指向实践应用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创新的。学术的本质特性,即‘学术性’的内涵至少包括研究性、学科性、创新性、理论性、科学性。”[1]根据这样的观点,学术活动的基础就是对大量资料的占有,而这也是档案编研工作的前提。
档案编研的基础是档案资源,丰富而又独特的档案馆藏是产生优秀编研作品的保障。南通市档案馆所藏张謇与大生档案,是张謇在个人与家庭生活中形成的,以及张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倡导兴办的企事业单位形成的,以文字、图表、声像等表达形式的历史记录,数量近万卷,不仅是研究张謇和南通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过程的珍贵社会记忆。档案是社会活动过程中直接形成的记录,这种原生性特征使得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档案得到更多的青睐。依托张謇与大生档案,南通市档案馆先后独立或与其它单位合作,编辑了多种史料汇编,如《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父爱如山——清末状元张謇写给儿子的信》《百年大生企业号信》等,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张謇与近代上海》是档案编研人员在大量研读张謇与大生档案的基础上,确定的编研题材。张謇与大生档案固然珍贵,也吸引了很多中外学者慕名而来,不过是提供了形成编研作品的可能。而系统地研读,除了需要一定的学识外,更多的是需要勤勉和毅力。何况这批档案数量可观,研读非一日之功。但如果不彻底浏览一遍,是无法真正体会其中的精髓的。
通过对档案的研读,结合已有的研究,笔者愈发认识到,张謇与上海之间关系的密切与重要,以及这种关系带给张謇、南通乃至上海的影响之深远。张謇时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张謇认为“沪地为万国竞争之场、商战之冲”。张謇经营实业的主要阵地在南通,而其实业上的兴衰成败,却与上海密不可分。在张謇的实业道路上,上海始终是其事业发展的依托。上海为张謇提供了从事实业的思路和模板,更为张謇输送了亟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是1872年在上海设立的轮船招商局,最早开办的纺织企业也设在上海。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采用了股份制形式,早期集资的主要区域是上海和南通,随后上海一直是张謇实业筹资的重镇。而盛宣怀创办的华盛纺织总厂是张謇学习的模板。人才聚集的上海也是张謇聘请技术人才,特别是外国技术人才的主要来源。而张謇也为近代上海经济、文化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认真细致的研读档案过程,是对张謇与近代上海之间关系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不断“相遇”的档案,有的印证了原有的猜想,有的拓展了认知,这些原汁原味的历史衍生品,不仅仅是还原了历史,更多是对当下的启迪。张謇创办事业过程,是不断接轨上海的过程,即不断吸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过程。对于今天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的南通来说,依然有着借鉴之处。
坐拥富矿并不意味着自然获取财富,还需要挖掘和提炼。与编研题材相关的档案,犹如散见于各处的珠宝,需要寻觅、串联,形成有机的组合。某种意义上,编研题材的确定与编研材料的选择,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启迪的过程。通过对张謇与大生档案的系统梳理,可以清晰地把握住张謇与近代上海之间的依托和互助关系,奠定了《张謇与近代上海》的编研框架。
2内容的加工与深入的研究
档案编研作品都是紧密围绕某个主题展开,以通常的档案史料汇编来说,在确定题材之后,不可能单纯地堆砌档案。档案的选择、考订、加工、排列,到标题的拟定、注释的拟写,都具有学术研究的特点。《张謇与近代上海》不同于纯粹的档案史料汇编,是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专著性质的编研作品。是从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出发,适当结合旧报刊资料,得出新的结论。学术的最终形式就是创新,创新也是档案编研作品的追求。因此通过对档案更加精准的选择,进而在研究上有突破,贯穿于《张謇与近代上海》整个编研过程。
2.1补充已有的研究
张謇与大生档案早已对外开放,但由于数量较大,也由于研究者各有关注点,因此张謇与大生档案难言已被充分利用。一旦编研课题确定,档案编研人员完全可能提供之前未被注意到的一些专业档案,有助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张謇是一位对中国教育有杰出贡献的教育家,他的名字与许多上海的教育机构联系在一起。张謇与震旦学院的关系,之前已有研究涉及,但都没有充分利用大生档案中的相关史料。震旦学院由马相伯始创于1903年,1905年因与总教习南从周在教务问题上意见分歧,马相伯率学生出走,另创复旦,震旦陷于停顿。张謇、李平书、姚子让等人合组校董会,帮助震旦于1905年8月正式复课。
张謇与大生档案中保存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下旬所立的震旦学院乙巳下学期收支账、丙午(1906年)正月所立的收支簿,说明在震旦复课后的账务是由大生沪所代理的,其中记载了大生多次汇来洋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震旦学院曾经为购买枪支弹药报关事宜致信张謇。据大生沪所三月十二日(4月24日)的来信摘录,震旦学院“第四学期即须添授军操”,因此委托意商义丰银行承运毛瑟枪120杆,子弹1万发,希望作为校董的张謇能够跟海关沟通,发给护照。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壬戌年底存在目录,记载“在震旦学校(旧欠)规银壹佰捌拾两零壹钱贰分贰厘”,即1922年底大生还为震旦学院垫付了百余两规银。
2.2修订错误的认识
大生最早的驻沪机构,名称为大生上海公所,暂寓福州路广丰洋行内。设立之时的功能,一方面是与江海关打交道,另一方面是作为集资场所。大生上海公所是大生最早设立的筹备机构,之后多次更名(沪帐房、总管理处、联合事务所等),也多次搬迁驻地,逐渐由大生驻沪联络机构演变为大生企业的枢纽,后人一般统称为大生沪所,是大生接轨上海的主要渠道,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提及大生上海公所时,都引用原大生沪所职员徐润周1962年的回忆:“1897年冬,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在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附设帐房。1898年迁设小东门,1901年迁天主堂街外马路。”[2]
1962年5月25日,由大生一厂党办秘书洪国辉赴上海,陪同徐润周、沈彦如、刘瑞尤、张爽清等四人赴南通,来回船票均在《大生资本集团史》的费用中支付,应该是为《大生资本集团史》提供口述。但是据徐润周1944年在大生纺织公司的人事记录,时年46岁的徐润周是“民国八年九月”进厂的,既不是当事人,又时隔多年,记忆难免有误。
1896年 1月26日,潘华茂、郭勋、樊芬、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等6位筹办纱厂的董事,联名向张之洞上奏了《遵办通海纱丝厂禀稿》。要求设立通海大生纱丝厂上海公所,通海纱丝厂是大生纱厂的初名,这个要求很快得到批准。因此大生上海公所应该是在1896年初设立的。1897年12月1日的《申报》第5版,刊登的《通州大生纱厂告白》,透露了大生纱厂的帐房,已经位于上海新北门外天主堂街。显然大生上海公所从广丰洋行迁出,并改名沪帐房,是在1897年下半年,这是大生沪所多次搬迁地址中的第一次。
2.3提出全新的观点
号信是以年为单位编号的信件,目前对于号信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张謇与近代上海》对大生的号信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号信是大生财务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大生财务收支和核算的依据。
张謇与大生档案中保存着大生沪所与大生一厂、二厂、三厂、天生港电厂以及各分庄、分销处的来往号信抄件(原信档案中无存)。南通市档案馆所藏号信,形成时间为1907年至1952年。号信一方面用于交流市场行情、人员动态和经营情况,更主要是用于沪所与相关企业之间的银钱往来。如目前可见最早的1907年大生纱厂致沪帐房元号号信,提及“厂讯二百五十八号,曾询会余交源生尾款九八元四千五百三十八两八钱九分九厘是否相符,未蒙示及,乞再一查。又二百五十七号讯寄去之四百廿四号票根之票未用退回,应请将原根寄厂。除夕厂中收存现洋十八万圆,如沪上需用时,或汇或解,俟示照办。今寄上四百廿五号票根一页,计洋五百圆,届期祈照兑。”[3] 1936年2月17日,《大生纺织公司总管理处办事细则》有关经济组的第56条规定,是这种做法的制度化:“出入款项应由号信陈述者,由总会计签注送文书股照写。”[4]
3质量的保障与题外的功夫
3.1注重实地走访
实地走访,可以跳出文献记载的局限,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对于研究者来说,能体味历史风云留下的痕迹,直接走入过往岁月的场景,有助于编研人员建立空间感、厘清思路。张謇与上海之间的联系,至今还有很多遗迹可踏访。南通自不待言,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等由张謇创办,又与上海关系紧密的单位旧址尚在。倒是散布上海各处的与张謇有关的处所,更值得寻访。
笔者主要踏访了已知的大生沪所所在地,从最早的大生上海公所,到天主堂街、紫来街同福里、小东门外城河浜、外滩十二号等处,再到大生自己建造在九江路上的南通大厦,到大生沪所最后的落脚处南京路保安坊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四楼。大生沪所驻地基本上都离现在的外滩不远,这一带是当时上海金融机构云集之处,便于与银行和钱业的沟通,距离十六铺大达码头也近,交通便利。九江路南通大厦2015年被上海市政府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现址有介绍文字:“裕和洋行设计,1920年竣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简洁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平面近似呈梯形,平屋顶,外墙为素色水泥粉刷。立面造型简洁。”南通大厦是大生事业巅峰阶段的标志,她静静地矗立着,无声地揭示着昔日的荣光。南京路保安坊其实与南通大厦相距不远,现存张謇与大生档案的主体在这里历经了动荡岁月,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使得张謇与大生档案成为今天的社会记忆。
3.2充分利用资料
档案编研以档案为根本来源,并不排斥对报刊、图书的参考和引用,特别是在对档案进行考证的时候,产生于同时期或者稍后的报刊和图书,是辨别档案真伪、补充档案不足的主要依据和来源。
馆藏资料由于获取的便利首先应该得到重视,南通市档案馆所藏的《私立震旦大学一览》,由震旦大学于1935年编印,其第一编《总述》的《校史》中,讲述了震旦的创立、复校和发展过程,记录了张謇对震旦作出的贡献,是对张謇与大生档案的补充。
馆外资料同样需要关注。任何收藏机构都不可能囊括所有的资料,何况一个地级市的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是一个资料的宝库,特别是其拥有的《密勒氏评论报》,是民国时期发表有关张謇及南通报道较多的英文报纸,可以让我们从西方人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张謇与上海之间的关系,因此相关报道也被选入《张謇与近代上海》。
各类电子数据库也值得参考。诸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上海图书馆的《晚清期刊、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爱如生的《晚清民国大报库》等,都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以《申报》为例,且不说大量的有关张謇在上海活动的报道,就其刊登的大生的广告,许多是张謇与上海关系的真实记载,在张謇与大生档案中也可以找到部分底稿。
3.3努力增强学识
编研人员的素质是档案编研作品学术追求的保障。编研人员首先要热爱档案工作,对编研要投入热忱。巴金先生有句名言:“我之所以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这句话用到档案编研上同样适用,没有情感的工作,必然是被动地完成任务,而有感情地参与,那是事业,会寻求超越和完善。
光有感情也是不够的,档案编研牵涉到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文史知识。就张謇和大生档案的编研而言,大量的手写文稿识别难度很大,其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还需要考证。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很难顺利完成工作。同时还要跟踪史学前沿,对于张謇与近代上海的最新研究动态,做到了然于胸,下笔方才有神。
参考文献:
[1]张威,谢镒逊.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学术性及其边界探讨[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6(03),101-108.
[2]《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 大生系统企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122.
[3]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B401-111-4.
[4]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B403-11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