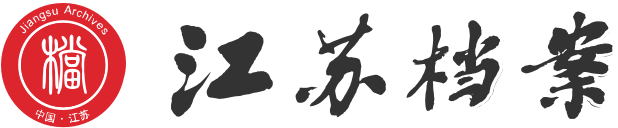- 信息时间:2020-08-12 11:03
- 浏览次数: 120
“人的死亡会有两个阶段,一是肉体的逝去,无法真实的感受这个世界;一是灵魂的逝去,当世界上再无人记起你时,便迎来了真正的死亡。”
我们天然恐惧死亡,恐惧被他者遗忘。当死亡变成一件确定会发生的事情时,便希冀于自己的行为轨迹被记录,自己的名字能在世间某个角落永存。继而,我们美化记忆,将记忆视为殿堂,而恐惧遗忘,将遗忘看作黑洞。
数字时代便利的记录与保存条件带动了现代社会记忆手段的不断更新,有关记忆的学科理论的深入研究引发了对数字记忆的相关讨论。冯惠玲教授曾对数字记忆进行了深刻阐释:“数字记忆是数字形态的文化记忆,携带文化记忆和数字信息的各种基因和特征,简单地说,就是将特定对象的历史文化信息以数字方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在网络空间承载、再现和传播的记忆形态。”[1]
而“遗忘”作为记忆的对立面却受到冷遇。让人不禁发问:“记忆”为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是否真如殿堂般美好,“被遗忘”的权利是否会得到尊重?或许这篇文章会给你一个答案。
 壹 遗忘权
壹 遗忘权 
 从一个超忆症患者说起
从一个超忆症患者说起 
学生时代,你是否幻想过自己会拥有“超能力”?在各类奇思妙想的“超能力”投票中,超强的记忆能力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青睐:比起炫酷但用处不大的飞翔能力、神秘但带有一丝恐怖色彩的隐身能力,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够让自己考试时减少大量的复习时间,继而成为考场霸主。随之在“知乎”等网络社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得了超忆症的人能成为学霸吗?”
超忆症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医学异象,属于无选择记忆的分支,临床表现为大脑拥有自动记忆系统。有超忆症的人利用左额叶(通常这个区域是用来处理语言的)和大脑后方的后头区(通常用来储存图片记忆)储存长期记忆。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在潜意识下发生的。具有超忆症的人,没有遗忘的能力。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能具体到任何一个细节。[2]
但当想象照进现实,超能力并不像脑海中那样美好。超忆症作为一种罕见病,没有确切的医疗手段进行治疗,却对每件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小学一年级时抢你橡皮的那位同学,或是初中做错的那道数学题,即使过去数十年,却依旧浮现在眼前。
Jill Price便是一位超忆症患者,她坦言,每当想起那些让自己悲伤的东西时,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当中。同时自己也常常因为回忆往事而影响工作,严重时还会导致失眠多梦,精神萎靡不振。[3]
超忆症患者所记住的,往往更是一种强迫反映,对自己痛苦的经历难以忘怀,而出现了各种心理疾病。同时,超忆症患者也会恒久地记住身边人所发生的经历,以致于被称作“人工谷歌”。对于超忆患者来说,生命需要遗忘,遗忘权对于他们这个少数群体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权力。
而与此不同的,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被遗忘权”,所谓被遗忘权,与超忆症患者所渴望摆脱的遗忘权不同,前者侧重于来自外部(包括他人、网络、档案资料等记录)的记忆,而后者则侧重于来自自身脑力的记忆。超忆症患者在人数上仍是少数群体,而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后,来自外部的恒久记忆则会令很多人患上了“数字超忆症”,带来痛苦的原因并非自身的记忆,而是互联网中所拥有的记忆。
 贰 被遗忘权
贰 被遗忘权 
 每人皆是数字时代的“超忆症患者”
每人皆是数字时代的“超忆症患者”
“由于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的发展,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 ——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
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伴随着互联网存储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被亲切地称作“数字原住民”。“数字原住民”生长于数字时代,居住于数字空间,同样自身的行动轨迹也会被数字永久保存下来,成为“数字超忆症”患者。与人的生理健康不同,治疗超忆症只需要根据脑科学治疗手段进行科学干预,而治疗“数字超忆症”这一社会现象却需要“被遗忘权”的赋予。
被遗忘权,简单来讲就是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着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所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这一概念的提出来自于欧盟发布的《一般数据保护规则》中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Erasure[4]。
(注:2018年5月25日,欧盟正式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
而这个数据概念保护的一般是个人琐碎数据,提出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人格权和个人信息权。随着被遗忘权立法的逐渐扩大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韩煦就“被遗忘权”中国本土化概念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可行性表现:一是个人信息公开的文化与网络无法遗忘之间的矛盾强烈的要求;二是信息主体具有确立被遗忘权的现实要素;三是我国目前存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做法的暗合被遗忘权。[5]继而引发了许多学者有关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相关讨论和关注。
 叁 判例分析
叁 判例分析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每当出现网络负面舆情事件时,总有人会坚信“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并据此呼吁人们重视身边的负面社会事件,然亦会有人反对,“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脑所能够挑选、记忆的事件极其有限,能够被反复提及、反复记忆的事件更少,从而会快速记忆,又快速忘记。
因此,应当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而使用互联网的群体记忆是有限的”,在互联网上的行动轨迹、发表言论、浏览信息都会被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自己的个人数据。“被遗忘权”所规范的主要信息,一是对自己不利的个人负面信息,二是个人不希望自己与之关联的信息。
个人负面信息,有轻微与严重之分,不构成严重犯罪的个人信息应当有被互联网遗忘的权利。2019年11月27日,德国柏林,最高法院裁定一男子拥有删除自己曾经犯罪报道的权利。此前,1982年该男子被控杀人。2002年获释,2009年该男子要求将各个网站中有关自己杀人的报道信息删除,以期消除影响,经过2012年一次请求驳回,在2019年法院通过了该男子这一要求。[6]这一新闻引发了广泛讨论,讨论的焦点一是在于犯罪记录是否应该在公众空间被删除,二是何种犯罪记录应该被删除,涉及重大刑事犯罪的犯人是否具有“被遗忘权”。
轻度个人负面信息,应当拥有存在时限和被删除的权利,既是对曾触犯过法律,在付出代价后人格权和名誉权的尊重,更是从“再社会化”角度讨论,为其重新融入社会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避免这类人群因被社会“过度记忆”而择业困难造成的生活困顿,再度犯罪。
个人不希望与其有关的信息,则有很多。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分手之后,自己都要忘记的名字,自己的输入法还在记得”。“被遗忘权” 正式出现在我国是2015年3月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任某某诉百度搜索公司一案。[7]任某某主张他在应聘时因其之前岗位身份——“晨睿智教育任某某”和“无锡晨睿智教育任某某”等字样影响其取得未来公司人事信任,从而间接导致了自己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无独有偶,在美国同样有人因为自己在经济困窘期在网络上做房产抵押而希望消除相关记录。其相同点在于这些人不希望自己与自己之前的身份标签——工作、社会关系、经济财产有任何的联系能够被想起。
这一心态实际上发生在每个人身边,每个人都迫切的希望删除个人社交网络中的“黑历史”,十年、二十年后回顾自己发表的朋友圈甚至会羞愧难当,但却会被别人拿出反复回味。因而,“被遗忘权”应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也都有权利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互联网同样也是人所操作和控制的。理想状态下,我们应当拥有个人信息能够被自己完全掌握的权利。
 肆 结语
肆 结语 
 谁来记忆,谁又来遗忘?
谁来记忆,谁又来遗忘? 
特里·库克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的文尾,对档案管理者的职业与记忆职责进行发问:这一代档案工作者希望为“文明”和“文化”制作什么样的礼物?当他们试图为未来馈赠一个过去的时候,又想让未来怎样来记忆他们?[8]已然将当代档案工作者视作记录历史、维系未来的社会记忆使者。
近年来,大量档案工作者以守护社会记忆作为目的,为记忆的保存和利用提出了大量有意义的学术观点。最终形成了以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教育机构为主的“社会记忆馆”场域,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良好的记忆条件。然在“被遗忘权”的讨论下,虽然在法学界尚未做到完全的法律本土化,但却也在为公民的这一权利进行充分的讨论,并逐渐受到重视。
就档案工作者而言,保持数字信息的长期存储是我们的任务,而未来对其中的个人数据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遗忘”也应是我们的责任。纸质档案时代因存储量的局限而导致的档案销毁情况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数字存储空间和先进的档案存储条件,在这一条件下,未来的销毁工作是否会走向个人信息的遗忘方向,是否会有与之配套的机制进行规范呢?小编的观点仅起抛砖引玉之用,在被遗忘权与档案、档案工作的结合上还有能够深入探索之处。这些问题有待各位读者在评论区与我们共同讨论哦 !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03):4-16.
[2]百度百科.超忆症[EB/OL].(2015-02-06)[2020-08-08].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5%BF%86%E7%97%87/10586165?fr=aladdin.
[3]SME科技故事.超忆症:虽过目不忘,但生不如死[EB/OL].(2019-10-31)[2020-08-08].https://www.huxiu.com/article/324019.html.
[4]王清华.个人数据应当有“被遗忘权”[EB/OL].(2018-03-30)[2020-08-08].https://mp.weixin.qq.com/s/6p1rAD19znfdBYqPJegK8Q.
[5]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2015(02):24-34.
[6]新京报.德国昔日谋杀犯获网络被遗忘权[EB/OL].(2019-11-29)[2020-08-08].https://m.weibo.cn/1644114654/4444094518346748.
[7]鑫士铭沙龙.”被遗忘权“首现我国判例[EB/OL].(2017-10-10)[2020-08-08].https://mp.weixin.qq.com/s/jzWcQ8u7to0661-CUuHXDg.
[8]特里·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李音,译.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作者:国际档案理事会中国宣传组
来源:2020.08.12 国际档案理事会微信公众号